
年轻时的叶企孙

叶铭汉(右)与叔父叶企孙(中)为数不多的合影之一

叶铭汉
在中国物理学家的谱牒上,叶企孙似乎是“被撕去的一角”。幸而,历史的蒙尘终将会被慢慢拂去,唤醒人们去探寻它真实的存在。
对于中国工程院院士、88岁高龄的叶铭汉来说,2013年4月20日,是他生命中值得被记录的一天。
吃过早饭,叶铭汉从位于中关村的家中出发,走路前往近一公里之外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像往常一样,老人尽可能让自己走得快些,这是他强身健体的一种方式,早已成为习惯。不同的是,他今天匆忙的脚步中多了一份急切的渴盼。
叶铭汉此行,是要去参加《叶企孙文存》发布会暨叶企孙诞辰115周年纪念会。他想尽可能早一些到达会场,出发前,还不忘检查是否将使用多年的卡片相机随身带好。
受邀嘉宾陆续到场,叶铭汉与前来打招呼的人一一握手,连声道谢,欣然与他们合影。这份感谢,不仅仅是他作为《叶企孙文存》编者之一,对来宾的礼节性表示。举手投足间,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叶铭汉那份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毕竟,他是这次纪念叶企孙先生的特别活动中,唯一到场的亲属代表。
这场算不得隆重的活动,在叶铭汉心中却是庄重——这是缅怀叔父叶企孙先生的一场特别仪式,深埋多年的一桩心愿最终得以实现。
遗忘
谁是叶企孙?时至今日,相信还有很多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叶企孙先生对上个世纪之初我国的科技界、教育界和老一代的清华人来说应该是声名赫赫。解放后,先生虽少有露面,但至少还有圈内人知道。而到了后来,特别是经过种种政治运动后,先生则彻底被人们遗忘。到上世纪末,已经没有人知道谁是叶企孙了。”
在《叶企孙文存》发布会上说这番话的人,是报告文学作家邢军纪。他曾用10年时间钩沉探微,写下40万字的长篇传记《最后的大师》,试图唤醒人们对叶企孙——这位“我们知道得最晚、被时代抛弃得最远的大师”的真切记忆。这部作品的缘起,则是受“两弹一星”元勋钱伟长之邀。
谈起新中国的科技成就,人们总会津津乐道于“两弹一星”的辉煌过往。只是鲜有人知道,包括著名的钱三强、赵九章、王淦昌、王大珩等在内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超过一半都是叶企孙的学生,或者是他学生的学生。
在中国物理学家的谱牒上,叶企孙似乎是“被撕去的一角”。邢军纪为叶企孙立传之初,受困于资料的极度匮乏,当时结集成册者只有钱伟长、虞昊主编的《一代师表叶企孙》,其余材料则零落各处。而让邢军纪更感艰难的,则是“当时语境对先生的挤压和屏蔽”。
这一切,皆源于避之不及的政治洪流。
受弟子熊大缜冤案株连,“文革”爆发后,叶企孙被红卫兵揪斗,关押、抄家、送“黑帮”劳改队改造,勒令他就“熊大缜问题”写书面交代,一度精神失常。1968年,受“吕正操案”牵连,70岁的叶企孙被逮捕,牢狱之灾中身患重病。一年后获释,他开始接受持续数年的隔离审查。
对那时叶企孙饱受磨难的生活,有这样一段令人心酸的描述:人们常看见海淀中关村街头有位行将就木的老人踽踽独行,或迎着北风仰天孤坐,穿着一条露出碎棉絮的破棉裤和一件捉襟见肘的旧棉袄,腰间扎根稻草绳,脚上趿拉着一双钻出脚指的老棉鞋,花白胡子及头发上结了冰……
钱三强曾在海淀街头偶遇叶企孙,赶忙走去跟老师说话。他却对钱三强耳语道:“以后你再碰上我,不要跟我说话了,省得连累你。”随即转身离开。
叶企孙终身未娶,身边无依无靠。自高中起跟随叶企孙的侄儿叶铭汉,当时亦被作为“反革命分子”下放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叔侄二人彼此杳无音讯。
“把他抓去时,也没有人来通知过我。我们当时没有任何联系,也不敢联系。”叶铭汉告诉记者,直到1972年回到北京,他才零星打听到一些叔父的消息,并提出要见叶企孙一面。
叶铭汉眼前的叔父几乎没有了人形,身患严重的丹毒症,两腿肿胀发黑无法行走、站立,前列腺肿大造成小便失禁,因而不能卧床休息,整日坐在一条破旧的藤椅上,身边堆满科学、历史或文化书籍。
此后,叶铭汉常去叔父家看望,但叶企孙从未向他谈及自己的遭际。“叔父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他一生很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他对自己的遭遇淡然处之。”
叶铭汉曾向叔父提出要为他的冤案鸣不平,叶企孙则对他摇摇头:“那很不容易,历史上有许多人物,他们逝世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结论,不仅是诗人、政治家、文学家,外国有许多科学家,在世时也很不得意,还受教会迫害。”
1977年1月13日,“文革”结束后三个月,叶企孙因长久病患溘然长逝。其生前所在的北大校方领导口头告知叶铭汉等家属,叶企孙问题仍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骨灰放在八宝山”。
叶铭汉曾要求逝世消息见报,却得到一句斩钉截铁地拒绝:“不是人死了都要见报的。”追悼会草草举办,叶企孙生前多年同事、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对悼词评价深感愤懑,中途退场表示抗议。
正名
仿似寒冬夜行人,曾经的“一代宗师”就这样在暗夜中悄无声息地诀别苍茫人世。“住进病房一天之后,叔父很快就过世了,没有留下任何托付。”而在叶铭汉内心,则早已许下一个要为叔父澄清身世、恢复名誉的心愿。
叶企孙离世两个月后的1977年3月28日,叶铭汉第一次致函统战部,请求过问叶企孙冤案,章明公理,从此迈上了一段艰难曲折的为叔父正名之路。
近一年时间过去,叶铭汉的请求未见任何答复。此后几年,他又先后致信北大党委、中科院、国务院等相关领导,表达叶企孙亲属昭雪冤案之诉求。叶铭汉的申诉,得到了吴有训、钱伟长等友人的积极支持。然而,信函在相关单位间批转往来,始终无法得到处理。
“要求平反并不是受到了很大阻力,而是根本没人理你。”叶铭汉这样描述当年遇到的困境。
转机出现在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国开始大规模平反冤案工作。北大党委为马寅初彻底平反,这让叶铭汉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1980年5月,北大党委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吕正操的平反决定通知书,6月作出结论称:“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逮捕叶企孙是错误的,强加给他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然而,这一结论并未能彻底澄清历史,叶企孙的名誉只得到部分恢复。
直到1986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关于熊大缜问题的平反决定”,其中特别指出,“叶企孙系无党派人士,爱国的进步学者,抗战时期对冀中抗战作出过贡献”。叶企孙弟子熊大缜47年前被定罪为“C.C特务”处死的不白之冤,由此得以洗雪。
一年后,《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文章《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以示完全恢复叶企孙名誉。
随着叶企孙冤案得以正式解决,国内科学史学界、物理学界的一些学者在钱伟长、钱临照等前辈的大力支持下,开始重新挖掘、梳理、介绍叶企孙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卓著贡献,回忆文章和书籍先后面世。在其弟子亲友的努力下,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纪念活动先后开展。
1992年,包括王淦昌、王大珩、吴健雄等在内的127名海内外著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联名者平均年龄高达72岁。1993年清华校庆,特在科学馆举办叶企孙生平照片及手迹展,参观者无不震惊钦佩。1995年,叶企孙铜像在清华大学第三教学楼门厅内揭幕。
然而,叶企孙其人其事在世纪之交并未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认知。2010年,央视著名记者柴静曾在博客中写下《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一文,记述自己知晓叶企孙片段往事的真切感触,一度引发公众热议,不甚唏嘘。
长久以来,只有为数不多的人通过零散的文字和影像资料窥得叶企孙生平片段,而对他本人遗留后世的珍贵笔墨却难得一见。作为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几个世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代表,他已成为时代的符号,其遗存的缺失实为憾事。
弥补这个缺憾,自然成为叶铭汉晚年生活的最大愿望。而叶企孙为学一世,长时间述而不作,公开发表的文章并不多见。在科学史界,自上世纪90年代起,收集、整理叶企孙遗存文著、电文、手稿,也成为同仁心中抹不去的心愿。
《叶企孙文存》的出版面世,最终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叶铭汉等编者将其视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份文化珍宝。这份工作的初步完成,让他们如释重负。
传世
谈及叔父叶企孙留给后世最为宝贵的遗产,叶铭汉说非学科教育和人才培养莫属。
在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及高教史上,1929年到1937年间的清华物理系,被认为是一个不朽的传说。大师云集、盛极一时,清华园内的科学馆,成为当时全国有志于科学报国的优秀青年心目中的圣殿。
此后对新中国科学事业作出卓著贡献的一大批优秀科学家,都曾在此聆听叶企孙的教诲。1929年,清华大学成立理学院,叶企孙担任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
叶铭汉本人的学术生涯,也与叔父叶企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1942年,家住上海法租界的叶铭汉收到叶企孙自大后方重庆发来的一封家书。叶企孙担心身处上海的叶氏家族受战事连累,恐遭不测,希望叶铭汉等家族后辈前往重庆继续学业,报考迁往内地的知名大学。
自幼,叶铭汉对叔父崇敬有加,树其为人生楷模,希望将来能像他一样以知识和修身在世间立足。读中学时,叶铭汉的学费均由叔父资助。收到家信后不久,叶铭汉与两个姐姐一同在战火中投奔重庆叔父。
1944年,叶铭汉考入西南联大,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了土木系。“当时是小孩想法,觉得到土木系学水利,能全国到处跑,将来也好找到饭碗。”叶铭汉说,对于自己的学业和人生选择,叔父并没有任何干涉,只希望他遵循自己的想法。
入学后不久,政府为提高抗战士兵文化水平,发动知识青年参军,叶铭汉爱国心切,深感应尽己之力,遂加入知识青年军参加抗日。
一年后抗战胜利,叶铭汉返校复学。1946年5月,西南联大复校为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在西南联大,我逐渐对物理感兴趣,加上我最好的一帮朋友都在物理系,在复校时选择转入物理系。”通过转系考核,叶铭汉如愿进入叔父主持的清华物理系。
然而在清华就读时,叶铭汉也并未受到叔父的特别荫蔽。他从未住过叶企孙家所在的北院7号,因为叔父对他说:“我希望你住在宿舍里,多接触同学特别是不同系的同学。我不希望你住在家里的原因之一,是家里老要讨论学校的事,你不应该知道,也怕你知道了传出去。”
“我念研究生也是自己的选择,叔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大学毕业后,叶铭汉决定跟随刚刚归国的钱三强学习核物理。钱三强正是叔父叶企孙的学生。由此,叶铭汉与叔父叶企孙有了进一层的师承关系。
硕士研究生的第一年,钱三强指导叶铭汉学习加速器相关知识。正值国家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展加速器研制,叶铭汉在导师的建议下离开学校前往参与国家这一重大任务。
与叔父叶企孙一样,叶铭汉在“文革”中遭受磨难,科研工作长期停滞。也许是考虑到自身处境之艰难,叶企孙在重病之下才表达了对侄儿叶铭汉能够作出科学贡献的期待。
在其生命末期,叶企孙拒绝侄孙叶建荣的就医劝告,并对他说:“其实,人无须活得太老,活得太老,最后几年就像熊冬眠一样,什么事也做不成,如果主政,还可能做错事。我一生想做的事,已经做完毕,还有的事,只好留待你铭汉叔父去做了。”
历经艰险之后,叶铭汉没有辜负叶企孙的期待。在核物理、加速器等领域,叶铭汉作出了他自己最为重要的科学贡献,成为我国低能加速器、低能核反应实验、粒子探测技术和高能粒子物理实验的开拓者之一。
众所周知,作为新中国重大科技成就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曾受到李政道先生的鼎力帮助。而在这份支持背后,则是李政道与叶氏叔侄二人,自西南联大起缔结下的深厚情谊。
在叶企孙存藏多年的一份遗物中,有三张泛黄的纸片,上面有叶企孙批改的分数:“李政道:58+25=83”。这份用昆明土纸印出的试卷,是李政道在西南联大时的电磁学考卷。叶企孙离世数十年之后,当叶铭汉将这份试卷拿给李政道看时,李政道感到慈爱师容如在眼前。
李政道与叶铭汉相知相识60余年,二人之友谊业已成为佳话。叶铭汉80岁诞辰之时,李政道回国参加庆祝活动,他这样评价老友的科学生涯:“铭汉兄从建设低能加速器开始,直到建设高能加速器,从2.5MeV直到2×2.2GeV,从建设碘化钠晶体闪烁探测器到北京谱仪,跃迁之高不可测量!铭汉兄从研究实习员到助理研究员,到研究员,到院士,跃迁之高亦不可测量!铭汉兄从小组长到大组长,到室主任,到所长,跃迁之高不可测量!”
2011年春,李政道为《叶企孙文存》作序,文中写道:“叶企孙先生是现代中国科教兴国的先驱者。”“我非常敬仰他,永远怀念他。”
“叔父叶企孙终会获得一份应有的正确评价。”叶铭汉相信,历史的蒙尘终将会被慢慢拂去,唤醒人们去探寻它真实的存在。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3-04-26 第5版 人物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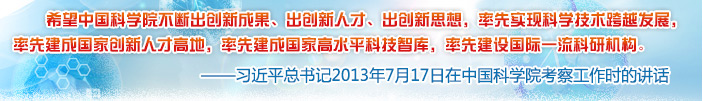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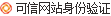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