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古气候学家丁仲礼院士带领一个研究小组,通过大量的计算,提出基于人均累积排放指标的全球各国未来排放权方案,在学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该年岁末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他又用研究数据直指目前一些主流的温室气体减排方案,如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方案、G8国家方案、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方案等有失公允。2010年7月19日,在北京三里河中科院丁仲礼的办公室,他就气候变化研究相关问题,接受《《科学新闻》》记者的专访时,话语间流露出的依然是严谨、率直的本色。
《科学新闻》: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2℃是人类社会所能忍受的最高升温限度,也就是2度阈值。目前全球碳减排的谈判,是为了防止全球气温升高2℃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变化吗?
丁仲礼:我个人认为2℃阈值主要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不完全是科学结论。以物种灭绝为例,IPCC指出升温2℃,可导致30%左右的物种灭绝。这个结论是模型计算的结果,依据是实验室对物种的一些控制实验。但研究者忽视了自然界的物种具有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比如可以迁徙。所以仅仅增温2℃就将造成灾难性后果的说法值得质疑,至少地质历史上增温后生物多样性增加这一普遍现象不支持“灾难性后果”这种预测。
尽管从科学的角度,2℃阈值存在很大的争议,但从控制增温这个目标出发,总得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以表明各国政府对增温的态度。所以我们要从道德层面去理解“2℃阈值”。
《科学新闻》:国际上的很多减排方案,如IPCC方案、G8国家方案等把IPCC提出的要将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450ppm(百万分之一)作为控制目标,你是如何看待这个目标浓度的?
丁仲礼:首先我要对一个基本概念进行纠正:IPCC所说的450ppm不是二氧化碳浓度,而是二氧化碳当量浓度(各种温室气体按照致暖效应折合成的二氧化碳浓度)。目前的二氧化碳浓度是389ppm,加上其他温室气体如甲烷、氧化亚氮等的折算,二氧化碳当量浓度已达到460ppm左右。你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目前超过了450ppm,还要以此为控制目标?这是因为IPCC报告认为人类排放的大气气溶胶可能起到致冷作用,大约可以抵消80ppmCO2当量浓度的致暖作用。
事实上,排放到大气中的气溶胶多种多样,有的起致冷作用,比如硫化物,也有的起致暖作用,比如黑炭。目前受观测条件的局限,对气溶胶气候效应的认识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以我“小人之心”度之:IPCC片面强调大气气溶胶致冷效应的目的,是为了夸大温度对二氧化碳浓度的敏感性,以推行他们的激进减排方案。因此我个人认为,IPCC将2度增温与450ppm二氧化碳当量浓度挂钩,缺乏科学证据。
《科学新闻》:你指出国际上的很多减排方案如IPCC方案等有失公允,你认为合理的减排方案和大气CO2控制的目标浓度有关吗?
丁仲礼:有关。一个目标浓度设定后,总的未来排放空间就随之而定,问题就变成如何将这一排放空间在各个利益主体间分配,目标越激进未来排放空间就越小,对不同的减排方案的争议就会越多。IPCC等方案的不公正性重点不在于目标浓度的设定,而在分配原则上。这些方案在全球未来排放权的分配上,违背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原则和共同而有区别责任原则。IPCC方案的本质,是给发达国家安排了比发展中国家多2~3倍的未来人均排放权。所以我们说,IPCC提出的碳减排方案,对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有它明显的政治倾向。换言之,IPCC是打着貌似公正的旗号,制定了一个不公正的减排政策。这也是发达国家政治家为什么要力推IPCC方案的原因所在。
《科学新闻》:IPCC得出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结论,主要是建立在已经发表的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但为什么目前会出现巨大的争议?
丁仲礼:争议并不是现在有,过去也一直有,原因很简单:气候系统太复杂,人类对其理解程度还很低。当然,IPCC对文献的选择性采用可能也是争议的原因之一。比如,6000年前的地球大气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当时的中国是仰韶文化时期,农业文明在全球范围内取得长足的发展。古气候研究界将这个时期称为“全新世气候适宜期”,因为这个时期有利于人类生存繁衍。地球历史上的冷暖交替过程中,暖的时期往往是雨量充沛、物种多样性丰富、生物产率增加时期。像这种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件,国际上也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几乎已是常识,但IPCC偏偏对其不重视。这样做难免会引起争议。
《科学新闻》:那么你怎样看待“气候门事件”?有媒体报道,英国科学家在选择支持IPCC结论的资料时,有意地忽视了部分与IPCC主流观点不一致的证据。
丁仲礼: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看待这个事件。一方面,IPCC的部分科学家在文献的取舍上,确实存在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忽略一些资料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个事件本身并不表明过去气温没有增加,也不表明气温的增高和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完全没有关联。我不怀疑人类活动可导致气温升高这个观点,但认为IPCC夸大了这个现象。IPCC称20世纪的增温主要由人类排放温室气体所致,但试想一下,最近100年(1906~2005)大气二氧化碳当量浓度升高了160ppm,气温只增加0.74℃。那么大气二氧浓度倍增(工业革命前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是280ppm,在此基础上增加一倍)后,气温将要增加多少度呢?简单算来是不超过1.3℃,而IPCC给出的结果是3℃。为保证它的结论说得过去,IPCC不得不祭出大气气溶胶致冷作用这杆大旗。所以现在问题的焦点不在有没有人类活动的影响,而是影响有没有被夸大。
《科学新闻》:我们知道,在IPCC报告中,援引中国科学家的研究结果比较少,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丁仲礼:在一些核心的问题上,比如刚才我提及的大气温度对二氧化碳浓度的敏感性,我国也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比如,中国科学家开发的两个模式(model)得出这种敏感性较低。但这些结果没有得到IPCC的足够重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处理不同模式结果的方式是取平均值,去掉了高值和低值;也可能是因为中国科学家的影响力有限,没有得到西方的承认。当然,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当今的中国科学家功利心太重,以项目争取、论文发表为目的,热衷于跟踪模仿,迷信权威,不敢质疑别人的观点,不敢选择有挑战性的问题,也不愿与同行通力合作,因而很少有原创性成果,也很少有集成性成果。一句话,拿得出手的东西不够多。
《科学新闻》:那么这是否因为中国科学家没有在国际主流期刊上发表论文吗?
丁仲礼:近些年来,中国科学家确实在国际核心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论文,但人家引不引用你是另一回事。发表的论文汗牛充栋,被引用者只是少数。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积累远不如别人,水平还不够。但我们在追赶,差距在慢慢缩小,不要妄自菲薄。
《科学新闻》: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成了社会热议的话题,你持怎样的观点?
丁仲礼:在我国,低碳经济作为一个概念,被媒体炒得很热,很多学者也在跟风炒作。但在国外的门户网站上,就很难看到这样的炒作。首先我介绍三个不同的概念: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
循环经济以充分利用资源为目标,可概括为3R原则,即Reduce(减量化)、Reuse(再利用)、Recycle(再循环)。
低碳是针对能源而言的,目标在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量。
绿色经济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方式。“资源节约”与循环经济关联,而“环境友好”不仅仅是指低碳排放,还包括各种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所以绿色经济是一个更加全面的概念,更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现实。
在现阶段,对“低碳经济”这个概念,我本人的看法是慎用,更不能滥用,因为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现实下,能源使用量还会快速增长,在能源结构难以实质性改变的限制下,我国的碳排放势必会增长。我们不能一边大谈发展低碳经济,一边增加碳排放量,这样会陷入逻辑困境。中国历史上人均碳排放很少、很低,而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是不可能不增加排放的。这点道理很好懂,应该向国内外讲清楚。不是低碳经济不好,而是我们近期内做不到。我个人对我国碳排放量的增加没有任何“负罪感”,排放量的增加是很正常的,除非你完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消除了贫困。
但是,展望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低碳经济也是会实现的,这要等到“低碳技术”成熟。低碳技术有两大类:节能技术和非碳能源技术。节能在中国有潜力,比如说,冶金、建材、建筑等行业能耗降低、发电转换效率的提升都有一定的空间,但这个潜力也是有限的。对非碳能源技术,要加大研发力度,但现阶段在应用上则要谨慎。因为碳排放是要计算全生命周期排放的。比如太阳能,不能仅仅考虑太阳能是可再生能源,还要考虑太阳能生产设备制造、安装、维护过程中的耗能和二氧化碳排放。
《科学新闻》:你如何看待比较有争议的水电问题?
丁仲礼:我是比较支持水电发展的。一方面,未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对电力的需求还会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可开发的水电还有很大的空间。但现在困扰水电发展的一个主要难点是移民的安置。如果在水库和水电站的建设运行过程中,能够考虑给当地居民以一定分红的机会,可能局面就会好一些。我不认为水电站的建设会造成很大的生态破坏,当然在任何电站建设前,必须做好环境评估。不能仅仅为了减少碳的排放,就忽略了生态环境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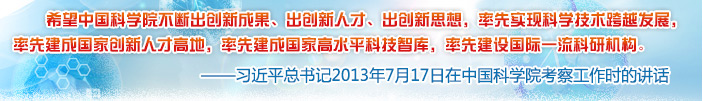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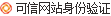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