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戴立信 祖籍江苏省句容县,1924年11月13日出生于北京。194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曾工作于上海钢铁公司、华东冶金局等单位。1953年,根据国家关于技术干部归队的部署,调至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工作至今,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和学位委员会主任,生命有机化学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金属有机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奖项。
人总是有对照,才更能体会到幸福。回想我这一生,经历过太多动荡日子,到了60岁后开始学吹打,才有了连续近30年的稳定的工作环境,怎不让人倍感珍惜。
我常常怀念曾经如同烛炬般指引我的科研道路的有机所老一代先生们,他们求实、求真的精神真正当得起德才双馨,我认为,这是一个科研工作者的最高境界,也是我一生所追求的目标。
国家的命运
加重了我的责任感
在浙大读书时,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积极参加学生社团,曾经担任了湄潭剧团团长,带领同学演出了《万事师表》《家》等。那段青葱岁月,真是叫人怀念。
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尽管如此,幸运的是还得到了科学的启蒙。
1936年,我就读于北平育英中学一年级时,正是抗日战争爆发之时,随着北平局势恶化,我随父母经青岛逃难至上海祖父家。到了上海不久,淞沪战争又起,进入了全面的抗日战争。转学上海后,我在初中换过两个学校,到高中,才算安定在三育中学完成。这虽是个弄堂中学,但教师队伍很齐整,高中化学课的老师很好,在当时的化学内容中竟然还有一些有机化学的内容。这也许是我一生从事有机化学的契机。
1942年我高中毕业,考取了沪江大学化学系。1943年春,因为战争形势日益严峻,我不得不辍学,随表姊及亲友多人结伴奔赴内地求学。有时步行,有时借助轮船、木炭汽车、小火车,一路途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贵州诸省而至重庆,跨越了日军封锁线。而后,经过教育部门批准,我开始了借读于浙江大学的生活。浙江大学当时位于贵州,新生部、工学院以及理学院、农学院又分处于永兴、遵义和湄潭三个县城。当时生活极为艰苦,上课、住宿多在庙宇之内,夜晚自修借助于几根灯草的油灯。但此时的浙大有竺可桢担任校长,竺校长广延人才,各系的教授都极负盛名,重视研究,学术气氛浓厚,曾被国外学者誉为东方的剑桥。
当时,化学系主任是王琎(季梁)先生,一位著名的分析化学家。教授有机化学的则是王葆仁先生。葆仁先生的板书最让我印象深刻,他画结构图非常漂亮,边讲课边板书,到下课时,留在黑板上的内容就是整堂课的总结,逻辑清清楚楚。在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又没有煤气的情况下,葆仁先生居然还千方百计地安排了许多有机化学实验(不比现在的实验内容少),也正是他将我引入了有机化学无穷乐趣的殿堂。
与有机所结缘
断断续续地做科研
在我的亲身体会中,对于科学家来说,“不折腾”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此也格外珍惜现在的好光阴。
1947年,我从浙大毕业,但那时,毕业就是失业。回到上海,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先做代课老师解决生计问题。还好,开年就有同学介绍我进入了位于浦东的第三钢铁厂化验室工作,总算是和学的专业沾上了点边。
那时,临近解放,我和厂里的工人兄弟们一起参加护厂运动,看见解放军进驻钢铁厂了,别提心里有多高兴。解放后,已经是党员的我,担任了上海钢铁公司军代表秘书的工作,后来又调到华东矿冶局,一直到了1953年,国家号召科学人才归队,我才由行政岗位被调至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工作至今。
终于回到自己的本专业,我特别珍惜。当时有机化学所刚开始开展高分子工作,庄长恭所长急需了解这些工作的科学背景和国际动向,于是,我便协助庄先生做一些文献工作。后来我又参加了黄耀曾先生领导的金霉素化学的研究,包括提取、分离性能研究以及金霉素的全合成研究。
这时我考虑到金霉素的绝对构型尚未确定,提出了用不对称合成方法来确定绝对构型的方案。这段时间前后,构象分析刚刚问世,我便和同事们一起翻译了两本构象分析文集和Newman的著名的《有机化学中的立体效应》一书。这些工作也是我后期工作的有利基础。
初学研究工作不到5年,1958年后,当时国家发展“两弹一箭”的工作中向有机化学提出了很多新要求,有机化学所结合国防任务开展了有机氟化学和有机硼化学的工作,于是我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参与了这部分的科技组织工作。当时一起参与这个工作的还有黄耀曾先生,接到这个任务,黄先生心里非常舍不得放弃已经有良好发展的手头工作,到新岗位报到的时候,他真情地说,觉得就像是自己的一个儿子死了。
但那时候的科学家都是以大局为重,为了国家的需求不惜放弃个人的得失。
当时,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比较超前的工作,比如我们研究了火箭推进器的燃料问题。和其他部门的同事合作,开发出了液氟的生产。
在原子能工业上要获得合乎要求的铀同位素,必须将六氟化铀进行同位素分离。起初,有苏联专家参与帮助我们做这件事,但不久,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离的时候带走了进行同位素分离的润滑油。没有这种特殊的润滑油,机器就不能运转;机器不能运转,就无法进行同位素分离。最后,有机所组织会战,在很短的时间内,自主研发出了这种机油,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直到1962年以后,我重返基础研究工作,独立地开展了当时问世不久的硼氢化反应的拓展工作和碳硼烷的化学。但这一段科研工作不久也因为那一时期的特殊原因被打断了。
之后的十年,我和很多同志一样,吃了很多苦。开始,我非常迷惑,最痛苦的是受到自己同志的打骂。但幸好,凭着一种信念,我挺了过来。
拨乱反正,小平同志的“科研是第一生产力”等教导给科学事业带来了新生。在百废待兴之际,1978年,在汪猷所长的安排下,我再次从事科研管理工作,做汪猷所长的助手,一直到1984年才开始重返科研第一线。
榜样的力量
怀念汪猷先生
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汪先生的音容笑貌,才华横溢的他曾用诗句提醒我们,科学研究者必须具有严谨求实的态度,因为:一旦功成千锤炼,不经意处百年愁。
汪猷先生是我国化学界大师级人物,他曾经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化学研究所,在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维兰德指导下当研究生。后来又去海德堡威廉皇家科学院医学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客籍研究员。在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库恩指导下进行藏红素化学的研究,做了博士后。回国后,他带回了德国人严谨的学风,身为有机所的带头人,可以说,他治所与治学一样严谨求实。
当时,整个有机所只有100多个人,真正搞研究的也不多。每天一早,汪先生就像医生查房一样,总是先到所有实验室转一遍,和每个研究人员对话,提问他们的工作进展。汪先生的专业知识惟有用“渊博”以概括,不管研究人员的研究课题是什么,他都能不断提问,直到被问者答不出了,他才转向下一个同事。汪先生就是用这样的训练方法来启发大家的思维。这正如当年在浙大时,李政道与我同学,他也曾总结道,学问学问,就要学会去问。
汪先生当时还兼任了化学学报主编,他是如此繁忙的一个人,用日理万机来形容,恐怕也不为过。但是,每到学报付印前,就算不睡觉,他也要把每一篇文章从头到尾地研读、修改。
1960年,汪先生和同事们在研究链霉素的立体化学中纠正了美国著名碳水化合物专家、链霉素结构的测定者沃尔弗浪姆等提出的链双糖胺β苷键的结论,确证为α苷键。在文章发表前,汪先生提出要做多种证明,坚持要做完才能发表。
正是在众多像汪猷先生一样的老一辈科学家的言传身教下,有机所建立了好的传统,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就是重视实践、重视实验。汪猷先生经常说,我的头衔首先是研究员,其次是所长,总是把研究工作放在前面的。
身为所长,汪先生对自己的要求格外严格,就我知道,那时除了工资以外,他一分奖金都不领。女儿大学毕业想出国深造,他没有写一封推荐信,但却为周围同事、学生写过很多。
做汪猷先生手下科技处长的那几年,我耳濡目染先生的一言一行,深味先生高尚的人格魅力,可以说,这也是我人生中所收到的一份来自于汪先生的珍贵无比的礼物。而前时期和黄耀曾先生一起工作时,黄先生对科学研究的执着、锲而不舍的信念,在科研事业中勇于探索、深入痴迷的精神,对我也是永志不忘的教育。
60岁学吹打
重返科研第一线
整整18年不在科研第一线,但我始终关心着有机化学文献,注视着国际上的最新发展,当我有了机会从事研究之时,我更是十分珍惜可贵的机会,力图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较好的工作。
在有机所像我这样的人有不少,我能成为有机所的第十名学部委员,有几个重要的机遇。首先一个机遇是,1984年汪猷先生和所党委决定,让我回到实验室从事金属有机、有机合成研究工作。这个时期正好是科学春天之后不久,或许是科学的夏天,应该是科学研究非常好的时期和条件,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在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时间最长的一段。
第二个机遇是,国家建立了研究生制度。研究生对有机所基础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有人说,没有研究生就没有有机所的基础研究,但真正要做好研究生的工作,这里面有许多工作要做。我有幸有一批非常有才华又非常勤奋的年轻同志和我在一起工作,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很大的帮助。
第三个机遇是,1953年的技术归队,中国科学院把我归到有机所,这样一个学术气氛很浓的一个所。我感觉,有机所有老一代科学家在30-40年代从当时化学研究中心的欧洲带回来的好传统,也有在50年代从当时的世界有机化学中心美国带回来好多新的知识、新的东西。在这么一个人才汇聚的大环境中,我的老师们、同辈们、年轻的同志们,大家相互鼓励,相互督促,奋发向上,真是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说到我个人的生活,我也非常幸运。有一位知书达礼、美丽温柔的妻子,已与我相伴了60个春秋!我们的女儿很理解我们的工作,从不要求我们的照顾,却给了我们很多的关爱,自己非常努力,现在在美国生活、工作。
去年,我不幸得了胃癌,但也许是凭着全家人割舍不断的浓浓亲情,我闯过了这一关,现在恢复得很好。不久前,我和妻子庆祝了钻石婚,我深深地觉得,我是一个幸福的人!
相关链接
戴立信早期从事金霉素的化学研究,包括提取、部分合成等。60年代的研究兴趣在有机硼化学,诸如α,β-不饱和醛酮的硼氢化反应,高级硼烷的衍生化反应,碳硼烷的合成及转化等和一些国防科技项目。80年代以后的工作多在有机合成、金属有机化学,特别侧重于通过金属有机化学的不对称合成等。这方面的工作有:环氧醇的开环反应研究及用于氯霉素的不对称合成,用于三脱氧氨基己糖全部家族成员的不对称合成等;铑催化的芳基乙烯的不对称硼氢化反应;具有C2对称性的氮配体,手性双齿配体的合成;钯催化的手性吗啉衍生物的合成;杂原子导向的、钯催化的、新选择性的温和羟氯化反应以及新合成方法学研究。此后的研究兴趣为立体选择性的合成官能团化的环氧化合物和氮杂环丙烷化合物等。曾有译著如《有机化学中的立体化学》及《有机化学结构与功能》等多部,编著《有机化学战略研究调查报告》《有机合成化学进展》及德国Wiley-VCH杂志出版的《不对称催化中的手性二茂铁——合成与应用》等书。

■ 上世纪50年代一批30岁左右青年科学工作者赴郊区(左三为戴立信)

■ 庆祝汪猷先生和黄耀曾先生从事化学工作五十周年,左二为戴立信,左三为汪猷,左四为黄耀曾,左五为女儿戴敬(当时为科技时报记者)

2010年5月钻石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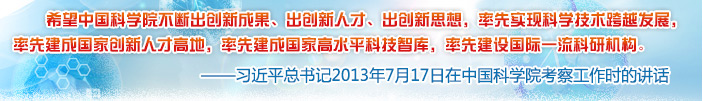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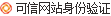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