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绝灭的真板齿犀(Elasmotherium)在其额骨上具有一只2米长的角,它一直生存到更新世末期,古人类将其形象绘制在洞穴壁画上,由此被认为是传说中“独角兽”的真实原型。所有其他的板齿犀都有一个或强或弱的鼻角,但真板齿犀似乎失去了其祖先的鼻角而突然获得了一个庞大的额角。板齿犀类从鼻角到额角的过渡一直很难解释,因为在具鼻角的祖先和具额角的后代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形态鸿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邓涛研究员等人在最新一期的《科学通报》英文版上报道了他们在甘肃临夏盆地的晚中新世红粘土中发现的一具大型的拉氏中华板齿犀(Sinotherium lagrelii)头骨,由此为真板齿犀的起源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这具中华板齿犀的头骨发现于临夏盆地内的广河县官坊乡槐沟地点,年龄约距今700万年。在此之前,中华板齿犀只有一些破碎的头骨和下颌骨残部以及孤立的牙齿发现于山西保德、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其角的发育状况一直未知。临夏盆地新发现的头骨证明中华板齿犀有一个向后位移的鼻角和一个较小的额角,因此它既不同于只有一个鼻角的宁夏犀(Ningxiatherium),也不同于只有一个额角的真板齿犀。显然,中华板齿犀是板齿犀类中从鼻角向额角转变的过渡形态类型,在进步的板齿犀中建立了进化和动物地理上的联系。
中华板齿犀头骨的鼻额部强烈隆起而粗糙,形成一个巨大而中空的穹窿,这一结构减轻了鼻骨和额骨的重量,与具大型鼻角的板齿犀,如宁夏犀平坦光滑的额骨区域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华板齿犀的鼻角角座向后位移到达额骨,并与一个较小的额角角座相连,角的如此组合形式在任何其他的绝灭和现生犀牛中从未出现过。其角座的背面有许多粗大的隆突,起到增加固着强度的作用;腹面有一个骨化的纵向鼻中隔,还有一系列斜向的侧肋,形成桁架结构,以加强支撑力,其机制与王莲的叶片结构相似。
由于中华板齿犀的鼻角变得相当庞大,即使有骨化的鼻中隔其鼻骨也无法承受其重量,由此造成鼻角向后位移。它的枕髁异常硕壮,与其他具大型鼻角的板齿犀或体型巨大的巨犀相似。板齿犀增长的头骨将对颈部产生更大的力矩,在保持大角的前提下,它们有两种策略来解决:一是鼻角向后位移变成额角,二是长头型变为短头型。这两种变化同时发生在真板齿犀的头骨上,因此其枕髁小于中华板齿犀,并因头骨变短而失去了第二前臼齿,而中华板齿犀的第二前臼齿仍然保留。新材料显示在进步的板齿犀中鼻角逐渐变大并向额骨位移,同时发育一个较小的额角,最后两角愈合成一个庞大的额角。这一发现解释了真板齿犀额角角座中央为何存在一条明显的横向骨缝,现在知道是鼻角角座和额角角座相互愈合留下的痕迹。
在先前的系统发育分析中,由于缺乏头骨,拉氏中华板齿犀的位置未能完全确定。临夏盆地的新发现显示包括中华板齿犀和真板齿犀在内的单系类群是可信的,而拉氏中华板齿犀是其中的最基干种,成为连接具鼻角板齿犀和具额角板齿犀的中间纽带。
中华板齿犀是体型巨大的犀牛,体重超过7吨,远大于最大的现生犀牛非洲白犀(3.2至3.6 吨)。长型的头骨、后倾的枕面、发达的颊齿次级构造、厚重的白垩质充填和褶皱的釉质为中华板齿犀提供了取食硬草和抵抗高纤维食物磨蚀的能力。拉氏中华板齿犀在晚中新世干旱频繁发生的中国北部生活于开阔的草原地带,与其生活在俄罗斯南部潮湿环境中的后代不同,由此否定了原来认为具额角板齿犀的祖先也生活于河畔的推测。
此项研究得到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973”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

图1 拉氏中华板齿犀头骨化石(邓涛供图)

图2 板齿犀类头部和角的进化(陈瑜绘)

图3 中华板齿犀生态环境复原(陈瑜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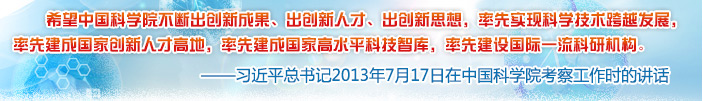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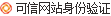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